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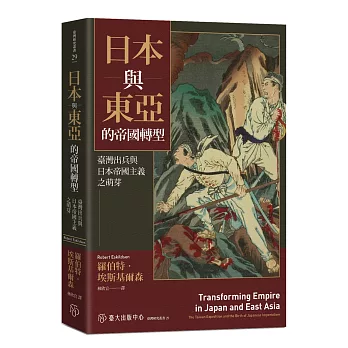
最近專注在東亞近代史的閱讀裡,上兩週拜讀了Robert Eskildsen的《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作者以甲午海戰前夕爆發的「台灣出兵」為切入點,分析日本人是如何透過西方近代國際關係的原則與清帝國博弈,以求伸張台灣番地(註:東岸)的利益與主權。作者以「遞迴帝國主義」的概念解釋日本帝國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動態互動,其中值得關注的部分在於「日本帝國是如何透過選擇性挪用西方近代文明的要素以對抗西方帝國列強」,最為明顯的例子是明治政府透過美國人處理「羅妹號事件」的模式取得靈感,並在「牡丹社事件」套用之。
本篇的《「同化」的同床異夢》的歷史場域落在了「乙未割台」之後的日治台灣,作者陳培豐梳理了日治台灣五十年間的語言同化政策、台灣人對於「近代化」的認知以及對於「國家/國體」的認同。若是從中國史觀的視角出發,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之下是「被壓迫的」、「被動且無力反抗的被統治階層」,直到「光復之後,國民政府從日本人的恐怖統治解放了台灣人」,然而陳氏在書中揭示的是台灣人是如何透過「國語教育」與台灣總督府、甚至是日本內地博弈,以求爭取平權的抗爭史。
「皇民化運動」一直以來都是大中華史觀者批判日治台灣歷史的利器,甚至引以為「台獨思想」之源泉,然而「皇民化運動」實則是昭和時期的政策產物,其對台灣人認同產生的影響是在日治後期,不應一概而論。陳著裡依照明治、大正與昭和時期劃分了日治台灣的語言政策,以「大東亞戰爭」為分水嶺,從而揭示了日治台灣的語言政策是如何從「溫和漸變」走向了「劇烈驟變」的過程。
在談論日治台灣的語言政策以前,首先得釐清日本人在治理台灣、朝鮮、愛奴、琉球(此四者甚至還能再行細分)與「大東亞戰爭」期間所佔領的太平洋群島、南洋等地的區別。前四者是在明治時期透過西方近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挪用而取得的主權,後者是「大東亞戰爭」時期急劇擴張而取得的領土。換而言之,日本政府有充裕的時間與理論基礎完善針對前四者的主權之伸張,後者則是赤裸裸的「戰果」。
台灣島是明治維新以來,首個透過戰爭與近代國關法則「依法」取得的領土,日本政府嘗試透過重構「國體論」以合理化殖民台灣的理據,然而「國體論」原先是為了鞏固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化成果而設計的理論,應如何重構並套用在治理異民族的台灣,乃至於後續的朝鮮、滿洲等地,這套思想之流變貫穿了日本帝國由萌芽乃至壞滅前夕的全過程。
前述的Eskildsen在《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一書中提及了「遞迴帝國主義」,談及日本政府是如何針對西方列強的進逼而作出相應的反饋,而在陳著裡亦可見相應的歷史痕跡:日本政府為了昭示己身與西方列強的不同,對外宣稱「台灣並非殖民地,而是大日本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此宣揚日本在道德高地的優越性。故此,儘管在日治初期英籍顧問Kirkwood曾經建議日本政府以英國治理印度的模式治理台灣,卻不被採納,其因在此。(詳見小熊英二著《「日本人」的界限》)
「國體論」固然是治理台灣的意識形態工具,然而在管治現場的前線不可能迴避如下問題:「漢民族居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是『日本人』嗎?」這是把持「國體論」的日本內地政府與管治前線的台灣總督府矛盾激化的根源,同時也是日本人與台灣人走向漫長「同化」的伊始。
日治台灣的語言教育政策在「同化於(近代)文明」與「同化於(日本)文化」兩者之間左右擺蕩。在日治早期的論述當中,台灣人固然是「日本人」,然而其落後的文明程度卻無法與日本內地相提並論,故此在台灣的教育現場應以「智育」(同化於文明)為先,迨及台灣人的教育水平足以與日本內地人相提並論之後,方可以「德育」之(同化於民族)。然而其中有個值得商榷的疑問:台灣人走向「近代化」的界限為何?
首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是貫徹「國體論」的典型人物,在「芝山巌事件」爆發以前,台灣的語言及教育政策是傾向於「理想主義」的「同化於文明」方針。初來乍到的日本人希冀透過教育資源的大量投放以促使台灣人盡早地走向近代化,然而此舉卻引發了統治危機:企圖透過近代化洗禮的台灣人據此向日本當局謀求平權。
前述「國體論」的「一視同仁」是建基於「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文明程度齊頭並進」之上的,能據此量化的就是台灣人的入學率。當台灣人的入學率已達一定程度時,總督府與日本內地自然不得不回應台灣人對於平等的訴求。以伊澤修二為首的「理想主義方針」在明治末、大正初告一段落,接任的持地六三郎等人轉而以「差異化統治」抗衡台灣人的平權訴求與來自內地左翼的「內地延長主義」(註:涵蓋台灣為「大日本帝憲法」的實施範圍,以此化台灣為日本內地的一部分)。
在觀察台灣總督府與日本內地政府在意識形態的拉鋸時,我們也不應該「虛位化」台灣人與日本統治者對抗的角色。台灣人在對抗日本統治階級不全是被動的,至少在「皇民化運動」之前,台灣人與日本人在「同化(民族或文明)」的詮釋之上仍是佔上風的。日本統治階級,尤其是台灣總督府方面並不具備論述高地以反駁台灣人的平權訴求。
前述台灣人積極響應台灣總督府的公學校教育體系並不應被籠統地視為「奴化」或妥協的表現,台灣人試圖透過選擇性挪用「同化教育」的戰術,「順從『智育』,反抗『德育』」,即便近代化教育是以國語(註:日本語)的形式呈現。陳氏定義國語/日本語為台灣人在攝取近代文明的「工具上的友性語言」,但同時也是「政治上的敵性語言」,然而這種模式卻使得台灣人在因應後續的「皇民化運動」時面對極大的心理創傷,因為台灣人發現在「皇民化運動」的強制推行之下,他們不僅在日常溝通之上,甚至連思考語言也免不了國語的侵擾。
書名題為《「同化」的同床異夢》,意味著臺、日雙方在「同化」的部分是有著重疊的共識,在統治初期因「美麗的誤會」而合作無間。然而隨著統治的推進,雙方開始逐漸了解對方的意圖,雙方的競合關係也逐漸傾向零和博弈,最終是以「皇民化運動」的順利推進而告終。
本書還有不少值得玩味的論述。若依大中華史觀者的視角觀之,「漢賊不兩立」的立場放在日治台灣的脈絡裡應是「『漢文書寫者』是堅持中華正統的台灣人,而『國語熟練者』是背棄祖宗的漢奸」,然而實情正好相反,尤其是在大正、昭和之交,當時的抗日份子幾乎都是以出身公學校教育或日本內地升學者(楊逵)為主,而不少的漢文協力者卻是以漢詩酬唱的形式應和台灣總督府的舉措。如此足證社會裡的意識形態光譜不應以某個單一要素以簡而化之。
留言
張貼留言